颜色之为物,想来应该像诗,介乎虚实之间,有无之际。
世界各民族都具有“上界”与“下界”的说法,以供死者前往——独有中国的特别好辨认,所库“上穷‘碧’落下‘黄’泉”。千字文也说“天地玄黄”,原来中国的天堂地狱或是宇宙全是有颜色的哩!中国的大地也有颜色,分五块设色,如同小孩玩的拼图版,北方黑,南方赤,西方白,东方青,中间那一块则是黄的。
有些人是色盲,有些动物是色盲,但更令人惊讶的是,据说大部分人的梦是无色的黑白片。这样看来,即使色感正常的人,每天因为睡眠也会让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失色。
中国近五百年来的画,是一场墨的胜利。其他颜色和黑一比,竟都黯然引退,好在民间的年画,刺绣和庙宇建筑仍然五光十色,相较之下,似乎有下面这一番对照:
成人的世界是素净的黯色,但孩子的衣着则不避光鲜明艳。
汉人的生活常保持渊沉的深色,苗瑶藏胞却以彩色环绕汉人提醒汉人。
平素家居度日是单色的,逢到节庆不管是元宵放灯或端午赠送香包或市井婚礼,色彩便又复活了。
庶民(又称‘黔’首、‘黎’民)过老态的不设色的生活,帝王将相仍有黄袍朱门紫绶金驾可以炫耀。
古文的园囿不常言色,诗词的花园里却五彩绚烂。
颜色,在中国人的世界里,其实一直以一种稀有的、矜贵的、与神秘领域暗通的方式存在。
颜色,本来理应属于美术领域,不过,在中国,它也属于文学。眼前无形无色的时候,单凭纸上几个字,也可以想见月落江湖“白”,潮来天地“青”的山川胜色。
逛故宫,除了看展出物品,也爱看标签,一个是“实”,一个是“名”,世上如果只有喝酒之实而无“女儿红”这样的酒名,日子便过得不精“彩”了。诸标签之中且又独喜与颜色有关的题名,像下面这些字眼,本身便简扼似诗:
祭红:祭红是一种沉稳的红釉色,红釉本不可多得,不知祭红一名何由而来,似乎有时也写作“积红”,给人直党的感受不免有一种宗教性的虔诚和绝对。本来羊群中最健康的、玉中最完美的可作礼天敬天之用,祭红也该是凝聚最纯粹最接近奉献情操的一种红,相较之下,“宝石红”一名反显得平庸,虽然宝石红也光莹秀澈,极为难得。
牙白:牙白指的是象牙白,因为不顶白反而有一种生命感,让人想到羊毛、贝壳或干净的骨骼。
甜白:不知怎么回事会找出甜白这么好的名字,几件号称甜白的器物多半都脆薄而婉腻,甜白的颜色微灰泛紫加上几分透明,像雾峰一带的好芋头,熟煮了,在热气中乍剥了皮,含粉含光,令人甜从心起,甜白两字也不知是不是这样来的。
娇黄:娇黄其实很像杏黄,比黄瓤西瓜的黄深沉,比袈裟的黄轻俏,是中午时分对正阳光的透明黄玉,是琉璃盏中新榨的纯净橙汁,黄色能黄到这样好真叫人又惊又爱又心安。美国式的橘黄太耀眼,可以做属于海洋的游艇和救生圈的颜色,中国皇帝的龙袍黄太夸张,仿佛新富乍贵,自己一时也不知该怎么穿着,才胡乱选中的颜色,看起来不免有点舞台戏服的感觉。但娇黄是定静的沉思的,有着《大学》一书里所说的“定而后能静、静而后能安、安而后能虑、虑而后能得”的境界。有趣的是“娇”字本来不能算是称职的形容颜色的字眼——太主观,太情绪化,但及至看了“娇黄高足大碗”,倒也立刻忍不住点头称是,承认这种黄就该叫娇黄。
茶叶末:茶叶末其实就是秋香色,也略等于英文里的酷梨色(Avocado),但情味并不相似。酷梨色是软绿中透着柔黄,如池柳初舒。茶叶末则显然忍受过搓揉和火炙,是生命在大挫伤中历炼之馀的幽沉芬芳。但两者又分明属于一脉家谱,互有血缘。此色如果单独存在,会显得悒闷,但由于是釉色,所以立刻又明丽生鲜起来。
鹧鸪斑:这称谓原不足以算“纯颜色”,但仔细推来,这种乳白赤褐交错的图案效果如果不用此三字,真不知如何形容,鹧鸪斑三字本来很可能是鹧鸪鸟羽毛的错综效果,我自己却一厢情愿的认为那是鹧鸪鸟蛋壳的颜色。所有的鸟蛋都是极其漂亮的颜色,或红褐,或浅丘,或斑斑朱朱。鸟蛋不管隐于草茨或隐于枝柯,像未熟之前的果实,它有颜色的目的竟是求其“失色”,求其“不被看见”。这种斑丽的隐身衣真是动人。
霁青、雨过天青:雾青和雨过天青不同,前者产凝冻的深蓝,后者比较有云淡天青的浅致。有趣的是从字义上看都指雨后的晴空。大约好事好物也不能好过头,朗朗青天看久了也会糊涂,以为不稀罕。必须乌云四合,铅灰一片乃至雨注如倾盆之后的青天才可喜。柴世宗御批指定“雨过天青云破处,这般颜色做将来”。口气何止像君王,更像天之骄子,如此肆无忌惮简直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不可为之事,连造化之诡、天地之秘也全不瞧在眼里。不料正因为他孩子似的、贪心的、漫天开价的要求,世间竟真的有了雨过天青的颜色。
剔红:一般颜色不管红黄青白,指的全是数学上的“正号”,是在形状上面“加”上去的积极表现。剔红却特别奇怪,剔字是“负号”,指的是在层层相叠的漆色中以雕刻家的手法挖掉了红色,是“减掉”的消极手法。其实,既然剔除职能叫剔空,它却坚持叫剔红,仿佛要求我们留意看那番疼痛的过程。站在大玻璃橱前看剔红漆盒看久了,竟也有一份悲喜交集的触动,原来人生亦如此盒,它美丽剔透,不在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,而在挖空剔除的那一部分。事情竟是这样的吗?在忍心地割舍之馀,在冷懒惰有的镂空之后,生命的图案才足动人。
斗彩:斗彩的斗字也是个奇怪的副词,颜色与颜色也有可斗的吗?文字学上斗字也通于逗,逗字与斗字在釉色里面都有“打情骂俏”的成分,令人想起李贺的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,那一番逗简直是挑逗啊!把寸水从天外逗引出来,把颜色从幽冥中逗弄出来,斗彩的小器皿向例是热闹的,少不了快意的青蓝和珊瑚红,非常富民俗趣味。近人语言里每以逗这个动词当形容词用,如云“此人真逗!”形容词的逗有“绝妙好玩”的意思,如此说来,我也不妨说一句“斗彩真逗!”
当然,“艳色天下重”,好颜色未必皆在宫中,一般人玩玉总不免玩出一番好颜色好名目来,例如:
孩儿面(一种石灰沁过而微红的玉)
鹦歌绿(此绿是因为做了青铜器的邻居受其感染而变色的)
茄皮紫
秋葵黄
老酒黄(多温暖的联想)
虾子青(石头里面也有一种叫“虾背青”的,让人想起属于虾族的灰青色的血液和肌理)
不单玉有好颜色,石头也有,例如:
鱼脑冻:指一种青灰浅白半透明的石头,“灯光冻”则更透明。
鸡血:指浓红的石头。
艾叶绿:据说是寿山石里面最好最值钱的一种。
炼蜜丹枣:像蜜饯一样,是个甜美生津的名字,书上说“百炼之蜜,渍以丹寒,光色古黯,而神气焕发”。
桃花水:据说这种亦名桃花片的石头浸在瓷盘净水里,一汪水全成了淡淡的“竟日桃花逐水流”的幻境。如果以桃花形容石头,原也不足为奇,但加一“水”字,则迷离荡漾,硬是把人推到“两岸桃花夹古津”的粉红世界里去了。类似的浅红石头也有叫“浪滚桃花”的,听来又凄惋又响亮,叫人不知如何是好。
砚水冻:这是种不纯粹的黑,像白昼和黑夜交界处的交战和檬胧,并且这份朦胧被魔法定住,凝成水果冻似的一块,像砚池中介乎浓淡之间的水,可以写诗,可以染墨,也可以秘而不宣,留下永恒的缄默。
石头的好名字还有入场多,例如“鹁鸽眼”(一切跟“眼”有关的大约都颇精粹动人,像“虎眼”、“猫眼”)“桃晕”“洗苔水”“晚霞红”等。
当然,石头世界里也有不“以色事人”的,像太湖石、常山石,是以形质取胜,两相比较,像美人与名士,各有可倾倒之处。
除了玉石,骏马也有漂亮的颜色,项羽必须有英雄最相宜的黑色相配,所以“乌”骓不可少,关公有“赤”兔,刘彻有汗“血”,此外“玉”骢“华”骝,“紫”骥,无不充满色感,至于不骑马而骑牛的那位老聃,他的牛也有颜色,是青牛,老子一路行去,函谷关上只见“紫”气东来。
马之外,英雄当然还须有宝剑,宝剑也是“紫电”、“青霜”,当然也有以“虹气”来形容剑器的,那就更见七彩缤纷了。
中国晚期小说里也流金泛彩,不可收拾,《金瓶梅》里小小几道点心,立刻让人进入色彩情况,如:
揭开,都是顶皮饼,松花饼,白糖万寿糕,玫瑰搽穰卷儿。
写惠莲打秋千一段也写得好:
这惠莲也不用人推送,那秋千飞起在半空天云里,然后忽地飞将下来,端的却是飞仙一般,甚可人爱。月娘看见,对玉楼李瓶儿说:“你看媳妇子,他倒会打。”正说着,被一阵风过来,把她裙子刮起,里边露见大红潞紬裤儿,扎著脏头纱绿裤腿儿,好五色纳纱护膝,银红线带儿。玉楼指与月娘瞧。
另外一段写潘金莲装丫头的也极有趣:
却说金莲晚夕,走到镜台前,把鬏髻摘了,打了个盘头楂髻,把脸搽的雪白,抹的嘴唇儿鲜红,戴着两个金澄笼坠子,贴着三个面花儿,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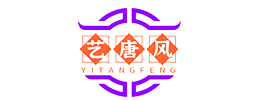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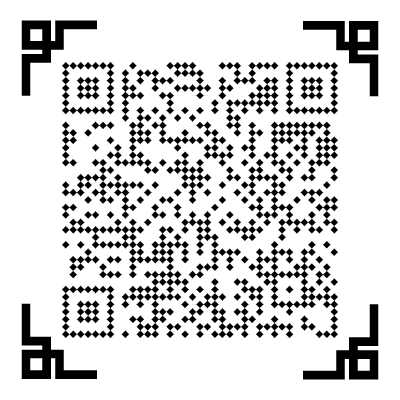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