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丽日晴天,坐在亭子里读陆延灿的《续茶经》,听书里的古人漫谈禅茶逸事,听微风袅袅落花依草的轻盈,也听流水潺潺睡莲在梦中的絮语,便觉着有无限的幽趣。
一本书,翻了三十多页,眼睛累了,起来走走,沿着竹篱小路折进一片竹林,藏青色裙裾飘逸的一角悠悠扬起,一阵清凉意漫过脚踝,竹影疏朗地映在地面上,风拖着三寸留白曳过苍蓝与葱绿交相辉映的天际,一声两声鸟鸣滴沥,不知从什么地方筛落下来,引人无限遐思。
一个人,抱着一本书,闲散地走在幽寂的竹林里,用大片大片幽素的绿意怡养眼睛,枯落的叶在脚下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,把一段寂然寂然的时间渲染得无比动听。
欲寻“一片茶烟出竹林”的逸趣,挽一缕烟霞,步入竹林深处,哪里有隐逸的人家?两三间草舍茅屋,四五棵山花幽艳,六七坛自酿的米酒,八九十样赏心好去处。门前流水,屋后竹林放养鸡鸭。
山居主人,春来,耕云种月,夜读诗书枕一片幽素入寐不知窗外春深几何;夏夜,竹簟纳凉,静观一径篱落流萤醉舞年光;秋时,凉亭小坐,自剥莲蓬尝一颗秋心清如水;冬至,踏雪寻梅,折一枝寒瘦插瓶作案头清供。
雨天,铺纸研墨,煮字疗饥。晴时,蒲扇熏风,竹叶煮茶。听茶,在风里咕咕清唱,一盏香茗未入喉,人已是醉了,《经锄堂杂记》云,“松声,涧声,禽声,夜虫声,鹤声,琴声,棋声,落子声,雨滴阶声,雪洒窗声,煎茶声,皆声之至清者。”
如此,眼里有云,有风,有竹,有叶,有花,耳听得云流,风动,竹喧,叶落,花拆。一壶清茶,文火细烟,水在壶里翻起细响,果声之至清者也。烧茶的人,手执一把蒲扇,温温雅雅地把西山残照扇落,把穿过竹林的晚风扇凉,把半坡野草闲花扇得甜甜酣睡了去。
火熄了,茶也煮好了。茶烟氤氲,香气清雅。煎茶的人,他知道我要来,尽管我们素未谋面,他是山居主人,而我,是云水过客,路过他文火细烟闲烹茶的时光,不敢打扰他的一心清明。
倚一株瘦竹,默然欢喜,也听云流,风动,竹喧,叶落,花拆,听水在壶里至清的声,听他拨弄竹叶细碎的响,茶烟迷了我的眼,泪水无声涌出来,不敢妄动,怕一不当心,便惊了这一份清宁。
他知,我是喜读茶味不懂茶的人,他倒一碗茶与我,轻白茶烟里,他的声音清清雅雅,与我说我未读到的《续茶经》里的禅茶逸事,“茶宜精舍,宜云林,宜瓷瓶,宜竹灶,宜幽人佳士,宜衲子仙朋,宜永昼清谈,宜寒宵兀坐,宜松月下,宜花鸟间,宜清流白石,宜绿藓苍苔,宜素手汲泉,宜红妆扫雪,宜船头吹火,宜竹里飘烟。”
我信,竹里飘烟,是诗章里最能打动人心的章节,他写,我读,竹里虚烟,茶香如故。我便静默在那一段茶烟熏得温软了的好时光里,向他讨一碗茶,不交换名姓,不诉说茶缘深浅。
红尘逆旅,我是喜读茶味不知茶的人,品不出煮茶的水是雪融水还是竹沥水,亦品不出碗里舒展的茶叶是摘自明前还是雨后,可有什么关系?饮茶的人,心情是宁静的,清朗的,不争的,不惨杂一丝一毫的红尘烦忧与凡俗妄念,目光相遇的刹那,心境澄和,不亦快哉?
别时,风烟俱寂,依然记着,他说,“茶宜清流白石,宜绿藓苍苔,宜素手汲泉,宜红妆扫雪,宜船头吹火,宜竹里飘烟。”皆清之至也,雅之至也,赏心之至也。赏心,不在多,三两枝就好,一曰竹林烹茶,一曰无心禅话,一曰入座半瓯轻泛绿。
那轻泛的绿,不是茶绿,是竹叶依依的绿,滴在溪流上,晕不出茶的形态,也晕不出禅的味道。我知,这世间,并无一个竹帚扫叶坐煎茶的人。竹里飘烟,亦非茶烟,那是柴米炊烟的味道,烟火得凡俗,也烟火得温暖,袅袅地散入竹林,透着饭菜的香。
我走尽屈曲蜿蜒的竹篱小路,不曾逢着一间草屋茅舍,亦不曾逢着一个逸世的山居主人,却遇见一溪清流,照见几竿修竹,照见一个布衣长裙素心人,照见她的茶想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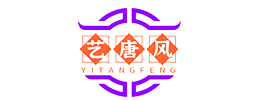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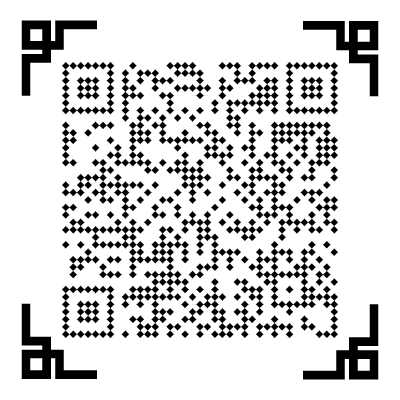
评论